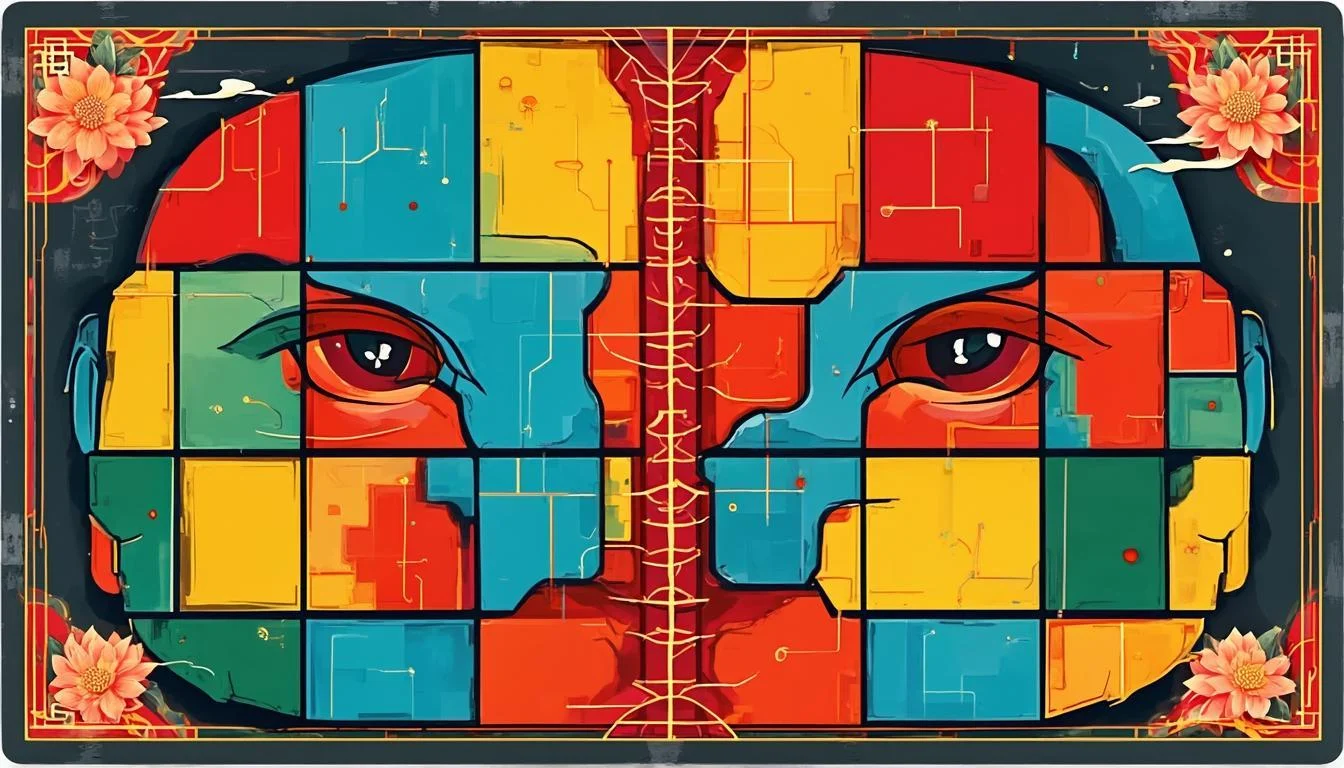
踏入长江商学院EMBA课堂之前,我以为自己做足了心理准备。作为一个在商海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创业者,我自认为见识过风浪,也懂得所谓的“商业规则”和“人情世故”。我来这里的目的很明确:学习更前沿的管理“术”,结交更高质量的人脉“网”,为我的企业再添几把增长的“火”。然而,几个模块的学习下来,我才恍然大悟,我所预想的一切,与我真正经历的相比,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我在这里遇到的最大“文化冲击”,并非来自某个惊天动地的商业案例,也不是某位教授颠覆性的理论,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、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颠覆。它不是一次性的巨浪,而是持续不断、温水煮青蛙式的价值体系重塑。
来长江之前,我的世界是一个由“术”(方法与技巧)构建的精密模型。我痴迷于商业模式的迭代、营销策略的优化、管理效率的提升和财务数据的分析。我像一个手艺精湛的工匠,不断打磨自己的工具,力求在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最优。我衡量成功的标准简单而直接:营收增长率、市场占有率、利润率。我以为,EMBA的课堂会给我一把更锋利的“屠龙刀”,教我如何更快、更准、更狠地攻城略地。
然而,第一堂课就给了我当头一棒。教授没有讲“增长黑客”,也没有分析最新的风口,而是在讲一家企业的“基因”与“使命”。他花了大量时间,引导我们这群早已在商业世界里杀得两眼通红的“成功人士”去思考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问题:“你的企业,为何而存在?” 这不是一句写在官网上的漂亮口号,而是一个需要用灵魂去回答的终极拷问。课堂上,我们讨论的不再是“如何做”(How),而是“为何做”(Why)。从曾国藩的“结硬寨,打呆仗”看战略定力,从罗马帝国的兴衰看组织生命周期,从王阳明的心学看企业家精神的内核。这种感觉,就像一个一心求取上乘剑法的剑客,却被师父要求先去挑水、砍柴、扎马步。
起初,我充满了困惑甚至是不屑。我认为这些“务虚”的讨论,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。但随着课程的深入,尤其是在与那些真正将企业做到百亿、千亿规模的同学的交流中,我才慢慢领会到其中的深意。他们关注的,早已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,而是整个战场的生态,是气候的变化,是脚下这片土地的可持续性。他们谈论的,是“利他”、“共生”、“敬天爱人”。我猛然惊觉,自己一直沉迷于“术”的精进,却从未抬头看过天,思考过“道”的方向。长江商学院带给我的第一个巨大冲击,就是强行把我的视线从脚下的六便士,拉向了天上的月亮,让我明白了“器”有形而“道”无疆的道理。一个企业走不远,往往不是“术”不行,而是“道”不明。
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,财富是绕不开的话题。在进入长江商学院之前,我对财富的理解,虽然不至于“拜金”,但也相对功利。财富是成功的勋章,是自由的保障,是社会地位的标尺。我努力赚钱,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,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,也为了在人群中获得那份应有的尊重。这个逻辑,看起来天经地义。
然而,在长江的同学圈里,我看到了对财富截然不同的诠释。我身边坐着的,有白手起家的实业巨子,有叱咤风云的投资大佬,他们的身家是我曾经难以想象的数字。但我发现,财富并没有成为他们言谈举止间炫耀的资本,反而更像是一种“甜蜜的负担”。一次晚宴后的小范围深聊,一位同学的话深深触动了我。他说:“钱赚到一定程度,就不是你自己的了,是社会的。你怎么用好它,让它产生比数字本身更大的价值,才是下半辈子要解决的课题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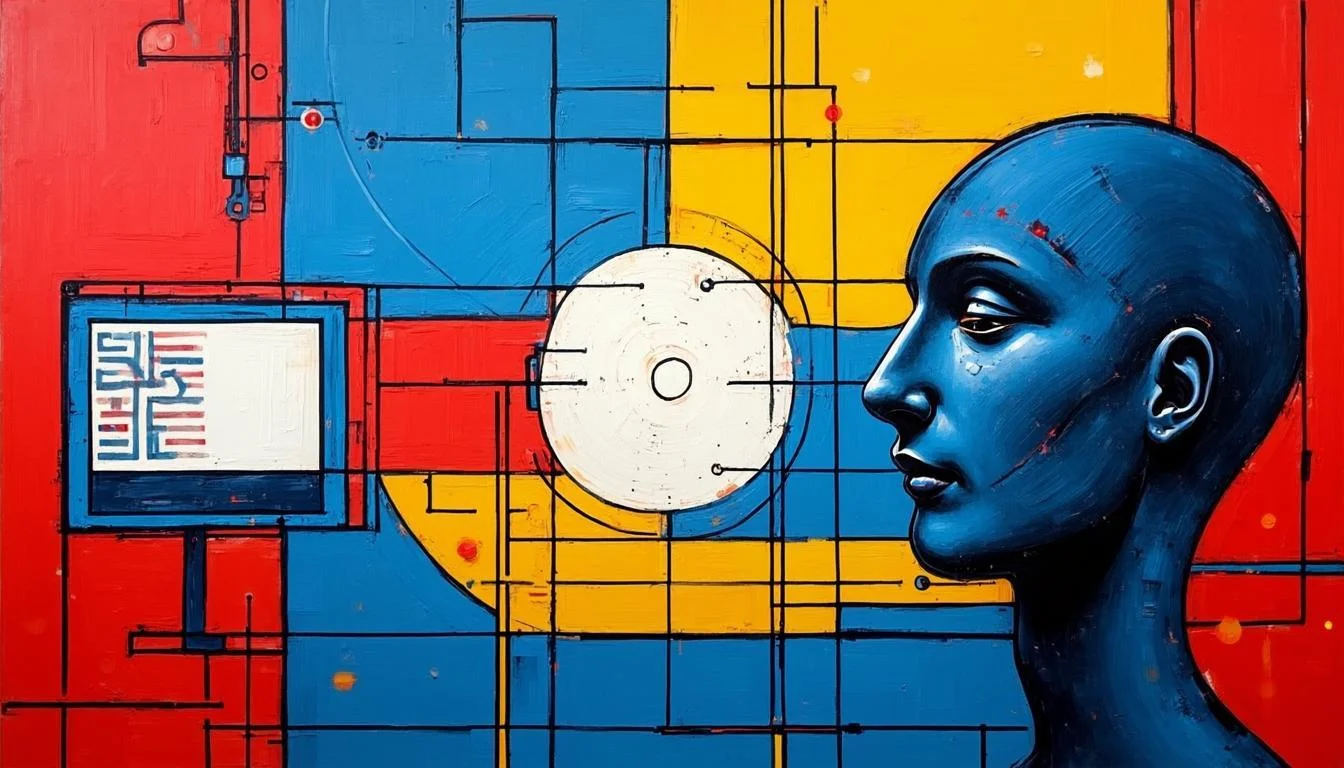
这种“财富观”的冲击是具体而微的。我看到有同学在主业之外,投入巨大的精力与财力,去做那些短期内完全看不到回报的公益项目,比如支持乡村教育、扶持青年艺术家、资助罕见病研究。他们不是简单的捐款,而是用运营一家公司的逻辑和标准,去系统性地解决一个社会问题。他们讨论的,是如何用商业的效率来做公益,如何让一分钱发挥出十分的社会效益。这让我深刻反思,我过去的慈善行为,更多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同情心或是偶尔的社会责任感冲动,而他们,已经将“社会创新”和“创造共享价值”内化为企业战略和人生使命的一部分。
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种观念的转变,我甚至在自己的笔记里画过一个表格:
| 维度 | 来长江前的我 | 长江同学们的普遍状态 |
|---|---|---|
| 财富定位 | 个人成功的终极目标 | 实现更大价值的工具和资源 |
| 使用方式 | 改善个人生活,进行再投资以追求复利 | 投入社会创新,解决社会问题,构建良性生态 |
| 核心关切 | “我能拥有多少?” | “我能成就什么?” |
| 精神状态 | 对增长的焦虑和对竞争的警惕 | 对使命的笃定和对未来的从容 |
这种冲击,让我从一个财富的“拥有者”,开始向一个财富的“受托人”转变。我开始思考,我的企业除了创造利润和就业,还能为这个社会留下些什么?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格局,也是一种更具挑战的修行。
长江商学院的课程设置中,有相当一部分内容,在实用主义者看来,是纯粹的“无用之学”。比如,我们会花整整一个模块的时间,去戈壁徒步,去感受历史的苍茫;我们会请来哲学系的教授,讲解东西方哲学的流变;我们还会欣赏昆曲,学习茶道,探讨美学。一开始,我对此非常不解。我们是来学商业管理的,为什么要去学这些“屠龙之技”?难道知道了苏格拉底和庄子的区别,就能让我的产品多卖几件吗?
这种“功利性”的疑问,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。直到一次人文课程中,一位历史学教授引用了庄子的名言:“人皆知有用之用,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” 他解释说,商业决策,尤其是在顶层的战略决策,往往不是一个逻辑推导和数据分析就能解决的问题。它更多地依赖于直觉、洞察力、同理心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。而这些,恰恰是那些“无用”的人文、历史、哲学才能赋予你的。
慢慢地,我体会到了这种“无用之用”的巨大力量。
我意识到,长江商学院不仅仅是在培养“商人”,更是在培养“企业家”。商人逐利,而企业家创造。创造,需要的恰恰是这些看似“无用”的土壤。这种冲击让我明白,真正的护城河,不是技术壁垒或市场份额,而是创始人和核心团队的认知深度和人文底蕴。当所有人都盯着“术”的层面激烈竞争时,那些在“道”和“识”的层面有深厚积累的人,才能实现真正的降维打击。
在来长江之前,我对EMBA的“人脉”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态。一方面,我期待能结识各行各业的精英,拓展我的商业版图;另一方面,我又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,担心这种圈子里的交往充满了功利和算计,每个人都像揣着一张资源置换表。我做好了准备,去进行一场场优雅而高效的“社交博弈”。
然而,现实再次给了我一次“文化冲击”。这里的“连接”,远比我想象的要纯粹和深刻。这种连接的催化剂,不是觥筹交错的晚宴,而是课堂上的激烈辩论、戈壁徒步时的相互扶持、深夜里毫无保留的“私董会”。在这些场景下,大家褪去了“董事长”、“CEO”的光环,回归到一个最真实的学生身份。你会看到,一个平日里在媒体上不苟言笑的行业大佬,在小组讨论中因为一个观点被挑战而急得面红耳赤;你也会看到,一个掌管着上万员工的企业家,在戈壁的帐篷里,和你分享他创业初期最狼狈的失败经历和内心深处的恐惧。
这种基于“共同学习”和“坦诚相待”建立起来的关系,其牢固程度远超基于利益的连接。我们不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,而是“同窗”和“战友”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棘手的公司治理难题,百思不得其解。在一个周末的晚上,我鼓起勇气在一个几位同学组成的小群里求助。没想到,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,几位同学,包括一位顶尖的律师和一位经验丰富的上市公司创始人,立刻和我开了一个线上会议,从法律、管理、人性的角度,帮我把问题剖析得清清楚楚。他们没有一个人问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回报,唯一的“要求”是,等我解决了问题,把复盘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的,是真正的“同学情谊”,是一种超越了商业利益的温暖和信任。
回过头看,我在长江商学院EMBA遇到的最大“文化冲击”,归根结底,是一场关于自我认知的“成人礼”。我带着一个“工匠”的身份走进来,希望能学到更精湛的手艺;但最终,我被引导着去思考一个“思想者”和“领航员”的命题。我曾以为商业的尽头是财富的自由,但在这里我发现,财富的背后是更大的责任和担当;我曾以为学习是为了掌握更多的“有用”工具,但最终领悟到,是那些“无用”的智慧,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;我曾以为人脉是资源和利益的交换,但最终收获了可以托付真心的友谊。
这次学习之旅,没有给我一张现成的地图,却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指南针。它没有直接回答我所有关于“如何成功”的问题,却让我开始持续追问“为何出发”。对于未来的企业家和管理者,我的建议是,当你考虑是否要投入时间和金钱去进行这样一次学习时,不要仅仅看它能教给你什么“术”,更要看它能否撼动你的“道”,能否为你带来一次深刻的“文化冲击”。因为,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真正能引领我们穿越迷雾的,不是手中那把日益锋利的剑,而是心中那座永远清晰的灯塔。

 同窗共度,携手追梦 |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
同窗共度,携手追梦 |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
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|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
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|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
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|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
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|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
 新生万物|听说,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!
新生万物|听说,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!
申请条件:
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(毕业3年以上)、国民教育大专学历(毕业5年以上)
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

长江商学院EMBA
关注官微
了解更多课程资讯
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
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
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
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