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坐在长江商学院宽敞明亮的教室里,身边围绕着一群在各自领域早已功成名就的EMBA同学。他们是上市公司创始人、是执掌百亿资产的投资人、是行业里响当当的领军者。我们交流的是产业趋势、管理瓶颈和全球化布局,每一次对话都充满了智慧的碰撞和资源的链接。然而,在某个瞬间,我的思绪会不自觉地飘向校园的另一端——那里,一群比我年轻十岁、甚至十五岁的MBA们,正热烈地讨论着某个商业案例,眼神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那一刻,一种奇妙的情感涌上心头,不是对身边EMBA同学的敬畏,而是一种对那些年轻MBA的、深深的羡慕。
这种羡慕,与成就、财富或地位无关。在这些硬性指标上,我的EMBA同学们无疑是顶尖的。这是一种更复杂、更微妙的情感,关乎于时间、可能性以及人生的不同阶段。它让我开始反思,当我们在人生的“收获季”回望“播种季”时,究竟在怀念些什么?
我羡慕MBA们,首先是因为他们手中握着一张几乎还未被填写的“人生地图”。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对于一个三十岁左右的MBA来说,商学院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加速器,更是一个转换器。他们可以从一个行业轻松地跃迁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行业,从技术岗转型到管理岗,甚至可以放弃之前的一切,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始新的事业。他们的每一次选择,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下崭新而大胆的一笔,未来充满了未知与惊喜。
这种“可塑性”是一种奢侈品,对于我们这些EMBA来说,早已遥不可及。我们的职业路径,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过去的成功所“锁定”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“路径依赖”(Path Dependence),它指的是一旦进入某个路径,无论是好是坏,惯性的力量会使你很难脱离它。我的EMBA同学们,包括我自己,事业已经高度成熟,我们是企业的掌舵人,身后是成百上千的员工和家庭。任何一次“转型”都不仅仅是个人的决定,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变革,其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高到难以估量。我们更像是在一条既定的高速公路上优化驾驶技巧、提升车辆性能,而那些MBA们,则站在一个拥有无数条道路的交叉路口,可以随心选择下一段旅程的方向。
时间,是世界上最公平也最残酷的资源。我羡慕MBA们的,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——充裕的时间。他们拥有一个更长的时间轴去规划人生和事业。他们可以犯错,可以尝试,可以失败,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,从头再来。对他们而言,一次创业失败可能只是履历上一段宝贵的经历;一次错误的职业选择,也可以在几年后轻松修正。他们有足够长的时间去等待“复利”的奇迹,无论是知识的复利、经验的复利,还是财富的复利。
相比之下,我们EMBA群体,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,但在时间维度上却显得“紧迫”。我们的决策往往追求更高的确定性和更短的回报周期。我们思考的是未来五到十年的战略布局,是如何实现企业的平稳传承,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。我们像是在进行一场精密的“收官之战”,每一步都需深思熟虑。而MBA们则更像是在下“开局之棋”,棋盘广阔,落子无悔。正如投资大师霍华德·马克斯在其著作《最重要的事》中反复强调的,承担风险并获得长期回报的前提是“你必须能够活到长期”。对于年轻人来说,“长期”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未来;而对于我们,则需要更审慎地定义和规划。

与可能性的无限和时间的充裕相对应的,是责任的轻重。我羡慕MBA们,是因为他们此刻正处于一种“轻装上阵”的状态。当然,他们也有学业的压力、求职的焦虑,但总体而言,他们最大的责任是对自己的未来负责。这种“轻”赋予了他们极大的自由,可以更纯粹地去探索、去吸收知识,可以为了一个纯粹的兴趣点投入大量时间,可以毫无顾忌地与同学辩论到深夜。
而我们EMBA,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沉甸甸的“甜蜜的负担”。这份负担是我们的企业、我们的团队、我们的家庭,以及社会对我们的期望。我们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,常常是一边听着教授分析最新的商业模式,一边用手机处理着公司的紧急事务。我们学习的目的性极强,总是在思考“这个理论如何应用到我的公司?”、“这个案例对我的管理有何启发?”。这种学以致用的精神固然高效,但也让我们失去了一部分纯粹作为“学生”的乐趣。我们很难像MBA那样,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,享受那种“无用之用”的快乐。
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差异,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格来对比:
| 维度 | 年轻的MBA | 身边的EMBA同学 |
|---|---|---|
| 主要关注点 | 个人职业发展、技能提升、探索新领域 | 企业战略、组织变革、资源整合、传承问题 |
| 决策风险 | 个人机会成本,影响范围较小 | 企业级风险,影响员工、股东及整个产业链 |
| 时间观念 | 长期导向,愿意为未来投资,容忍试错 | 中短期回报与长期战略并重,决策效率要求高 |
| 学习心态 | 探索式学习,吸收知识,构建体系 | 应用式学习,解决问题,寻找方案 |
| 生活状态 | 相对自由,生活重心围绕个人成长 | 多重角色叠加,需平衡事业、家庭、学习与社会责任 |
最后,这种羡慕也源于学习心态上的微妙差别。在长江商学院这样顶级的学术殿堂,知识的传递是平等的,但接收者的心态却截然不同。MBA们像一块海绵,贪婪地吸收着一切新鲜的知识和理论。他们对商业世界充满了好奇,每一个案例、每一个模型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认知。他们的提问往往是基础而深刻的:“为什么是这样?”这种追根溯源的求知欲,是构建坚实知识体系的基石。
而我们EMBA的学习,则更像是一次“知识重构”和“经验印证”。我们带着满身的实战经验和管理困惑来到课堂,试图从教授的理论中找到解释我们过去成功或失败的“密码”,并为未来的挑战寻找“药方”。我们的提问常常是:“教授,这个理论在我们的行业如何落地?”这是一种高效的成人学习方式,但有时也限制了我们跳出固有框架去思考。我们习惯于用过去的经验去“套”新的理论,而不是让新的理论去“颠覆”我们的认知。我羡慕MBA们那种不受经验束缚、天马行空的思维碰撞,那是一种能够催生真正创新的原始力量。
长江商学院的教授们也深谙此道,他们为我们EMBA设计的课程,往往更侧重于战略思维、哲学反思和全球视野,旨在提升我们的格局和境界。然而,我依然会怀念MBA课堂上那种为了一个基础模型争得面红耳赤的纯粹与激情。那是一种属于青春和探索期的特权,一种不再属于我们的奢侈。
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:我为什么会羡慕那些比我年轻的MBA,而不是身边的EMBA同学?
经过一番剖析,我明白了这种羡慕并非对自身状态的否定,而是一种对生命不同阶段独特价值的欣赏和致敬。我羡慕的,是MBA们所代表的可能性、时间、自由和纯粹的求知欲。这些特质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自然消退,被成熟、责任和成就所取代,这本身就是生命的规律,无所谓好坏。
这次在长江商学院的EMBA经历,其重要性不仅在于知识的获取和人脉的拓展,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场域,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MBA群体,从而引发了这次深刻的自省。这种“羡慕”提醒我:
或许,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探讨,如何在高管教育中更好地融合MBA的创新精神与EMBA的实战经验,创造出一种跨越年龄和阶段的“共生学习”模式。而对于我个人而言,这次羡慕之旅的终点,是与自己和解。我不再仅仅是羡慕他们,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将那份属于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,注入到我当前的人生阶段中。毕竟,在长江商学院这个平台上,我们不仅是彼此的同学,更是相互映照的镜子,照见过去,也照亮未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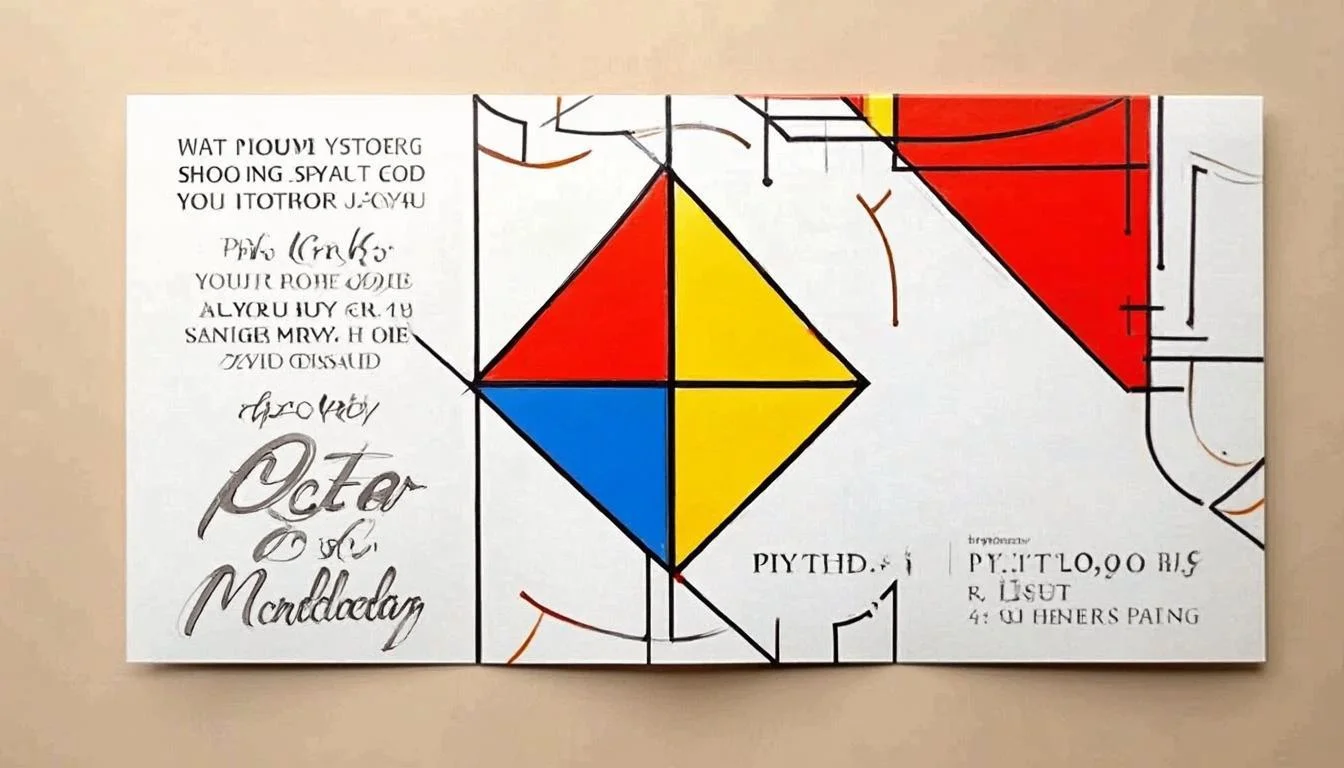
 同窗共度,携手追梦 |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
同窗共度,携手追梦 |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
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|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
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|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
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|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
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|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
 新生万物|听说,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!
新生万物|听说,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!
申请条件:
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(毕业3年以上)、国民教育大专学历(毕业5年以上)
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

长江商学院EMBA
关注官微
了解更多课程资讯
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
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
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
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